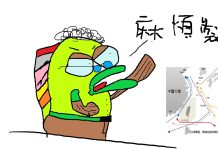生活總像潮汐一般,不斷漲退著相同的憂喜。而沉悶的課業與例行公事參雜其中,就像數不清的磨人砂粒。在這種疲憊的時刻,我已遠去的那段記憶,總在時光的支流中迂迴前來,喚出我勇氣的泉湧。在那段處於基測壓力的年紀,繁忙的課業、社會固有的規則,如同一個個透明的魚缸,將我囚禁其中,任水漂洗失去自己獨有的色澤與味道。於是我開始對於流浪有種浪漫的想像。看著電視所報導的外國流浪者,想像他們拍手擊板,一路馳唱,穿過疊疊荒野、星空,直至抵達海洋與夢境最深處,終生演出一場華麗的表演。
我深羨著這樣的狂野與叛逆,心裡暗想,為什麼我不能拋下那些加諸在我身上的責任與期待,只是自由的做自己想做的事?看著父親每日重複上下班,如同社會裡千萬張蒼白匆忙的身影一般奔勞,彷彿被某種古老狂熱的信仰所驅使,是那樣義無反顧的忙碌。而我,卻只想掙脫這樣的束縛。
存著這樣的念頭,在一次考試失利後,我決定出外旅行,深信著每人的體內,都有一個想要逃脫世俗、想要闖蕩的靈魂。於是整個城市的風景地圖便朝我蔓延開來,每個岔口都藏著我未曾體驗的意象,每個陌生的聲音都等待被聆聽。
簡便的收拾了行李,撘了公車來到火車站,擁擠的人潮有著不同的口音、身形與樣貌。同樣的是,每個人都背負著自己的失敗與偉大,有著被賦予需要抵達的地方。說是旅行卻又迷惑了起來,思索這是否是人類無可違逆的宿命。而一群席地而坐的遊民,就在此時映入了我的視野。他們以隨意的舉止,脫離於人群之中,像重複播放的老電影,以其灰淡緩慢的腳步,隱密地持續行走於這座城市。這樣的步伐,明顯與我一直遵從的規範背道而馳,那是放逐還是逃離?社會、家庭、責任、成就,這些名詞,他們又是以何種方式來解讀?
我決定暫停遠行,留下觀察這群沉默旅人的遷移。是的,旅人。我在心裡悄悄如此稱呼他們,自由漂浮、悠游的穿越一切,以這樣凝視而不介入的角度,旁觀這城市的愛恨情仇。我暗暗猜想,他們這樣的行走帶有著何種暗示?是否在進行一種長期的抗爭,以突破社會框框的束縛?便這樣滯留,客途於此,買了食物與清水,卸下我的手錶與手機,以及帶有些許不安的等待。隨著天色暗去,越多的旅人漂浮進車站,灰色的面孔與影子,逐漸佔據每個座位。白日的喧鬧與轟隆車聲已不再,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時而靜默,時而悉悉嗦嗦的聲響。
隨著夜越靜,只聽到無數緩慢、低沉的呼吸聲,陸續在空曠的大廳裡響起,像在低喃著只有他們熟識的神祇。是在做一場大規模的祭典吧!在每個夜裡約定於此,以繁華落盡的歲月作為祭品,只餘呼吸持續著禱告。想像其中的神秘聲色,我竟像是踏入了長夢的迴廊,走不出去。
於是停留在這個陌生的國度,與他們睡同一張椅子、同樣的睡姿。看著同樣的人群往來,這樣頹廢的生活和以往分秒必爭的升學生涯明顯不同,縱意卻又比想像中乏味。奇怪的是,當我完全放棄時間時,時間的流逝便變得無足輕重了,我感覺自己像是一隻發軟的魚,毫不在意自己在時光海流裡滑過了什麼。
在這段時間裡認識了老人丙爺,圓臉的他有著圓滾滾的大肚子,以及平和的氣質。我的爺爺也是身材肥胖。也因此感到他讓我特別親近,便這樣與他一起學習徘徊與默坐,思索與遺忘。也知道了半夜肯德基有賣剩的炸雞,半夜的車站只能出不能進,要早點進來,諸如此類的旅人密碼。日子過去,開始有人好奇詢問我是不是翹家,有人則鬼祟的說要介紹我「工作」。有人則感嘆年輕人不學好,若不是自己沉迷六合彩,也不會流落街頭。他们說,世代都有這樣的年輕人。說完又叨絮著許多感嘆。
這也是我第一次聽遊民的抱怨,說是觀察,畢竟也不好意思主動詢問。更多的遊民接著埋怨,有人怪自己年輕時不長進,但多數遊民只是怨恨著社會的不公。夾在這些人之中,我初次感到彆扭,自己像突然成了他們一塊不小心丟失的夢想拼圖。我可以深深感受到他們欣羨著我年輕的生命,而我此刻卻坐在他們之中。在越響越大的咒罵聲裡,只有對於光明的嘲弄,和一片的猙獰。我開始覺得有些不舒服,原來他們竟不如我想像中一般自由豪邁。那麼究竟是誰造成了他們在這裡?人生是由自己的抉擇所決定嗎?我此刻又為什麼會在這裡?
我的思想開始渾沌不安。
想法影響抉擇,既而帶來了一連串的改變,也許人生裡的行動都是變故,我也是自那時候開始明白的。我無意間看見一幅景象,丙爺在東張西望後,把殘存的飲料罐拿起來喝,我不知道要若無其事的走過還是避開眼神。
他們這樣的舉動,其實自己也知道是卑微的嗎?
那天晚上,丙爺笑咪咪的說要請我吃炸雞,看著店內來往的人潮,我又作了另一個決定。我停步了,怯怯地說:「我去便利商店買飲料請你喝,你進去拿好不好?」當我自便利商店出來時,丙爺的手上已經拿了一袋塑膠袋裝的炸雞。
我無法忘記他當時的眼神。
他看我的眼神很古怪,帶著一種嘲弄和無奈,有著悲傷和了然。又有著生活的不屈和理直氣壯。我低頭不敢看著他,他知道我在想什麼。走回火車站的路上,他慣練的穿越道路,似乎已走過這條乞食的路徑無數次,我也知道他發胖的原因了。我內心裡百感交集,夾雜著羞愧、不安、領悟等等情緒。我發覺我其實早已意識和他不是同種人。那麼我在這裡做些什麼?藉著嘲弄他們來纾解自己的生活壓力嗎?這些事情,當我出發時,便該知道了。
從這時起,我對他們的觀察起了全新的變化。我開始發現他們多數時候是緩慢不靈活的,彷彿滯留於過去,而不存活於當下。許多人只是長久的沉默坐著,紮根似的埋下肉身等待生滅。解開了社會所有的束縛,他們卻如株植物般糾結於地,只是時而凝視著繁複的指紋,彷彿不斷自問自答著不明的身世。這樣的謎題太繁奧,我無法回答,只在等一個答案讓我離開。而夜晚總伴隨著思索而來,時間流逝的恍若靜止,我躺在椅子上,身體極度渴睡,知覺卻異常清醒。於是轉頭望著隔座的丙爺,在昏黃黯淡的午夜燈光裡,他凌亂的髮浪,彷彿像是一汪垂暮的海洋,隱藏許多不可訴的哀傷。他就那樣蜷曲著睡著,一邊低喃著
不明的臆語,如不斷在睡夢中思考著生命和消亡。
望著他佈滿風霜的臉龐,我想起家裡的爺爺也跟這位老人是差不多的年紀。我忽然感覺有些羞愧,自己竟將這種無奈的漂流,當做一場瀟灑的旅行嗎?
我想撫摸他滄桑的臉龐。在相處中,遊民們已親切的成了我的朋友,就像我升學生活中的那些朋友一般。而這些漂浮的朋友,依靠的卻是無根的地舖,我深深感到命運的曖昧。作為兩種人之間區分的,又是什麼呢?
默默看著他的睡臉,我若有所悟。我自座位上緩緩的站起身來,彷彿初生見到世界一般,茫然又無懼。在長久的觀察和反思中,我開始明白了一些事理。自由,是建立在完成某種條件之後才能成立的。若想扔下未完成的責任,很諷刺的,反而會被更多事物緊縛,沒有人能真正脫離社會所訂下的規則,因此,無止盡的哀傷與自責,便是浪人們終生甩之不去的魔咒。
社會的種種規範雖惱人,但是在某方面,也引導我們走向正途,強迫我們面對種種難關與壓力,粹煉智慧,才懂得選擇自己的道路。唯有完成自己生命中的責任,才能真正的得到自在與歡愉。其實,每一個苦苦奮鬥,勇於承擔責任的平凡人們,又何嘗不是我所崇敬的勇敢旅行者。在人生巨浪無情的沖刷、掏洗中,兀自挺直身軀在苦途裡完成飽滿的自己。
挺直身軀前進,大都市的火車站像一頭形構複雜的猙獰巨獸,穿越過無數曲折的道路。穿越過旅人們囚居的層層心事,我在找出口,儘管前方的通道狹長黑暗,但曙光即將升起。我又一次想起了那時的我,我知道生命是一壺冷藏的酒,在密封壓縮中發酵成長。冬季甦醒雖然艱難,我感覺體內有些什麼悄悄的在長成。像光、像火。
(本文為讀者投書,也是履行了一個事隔多年的承諾)